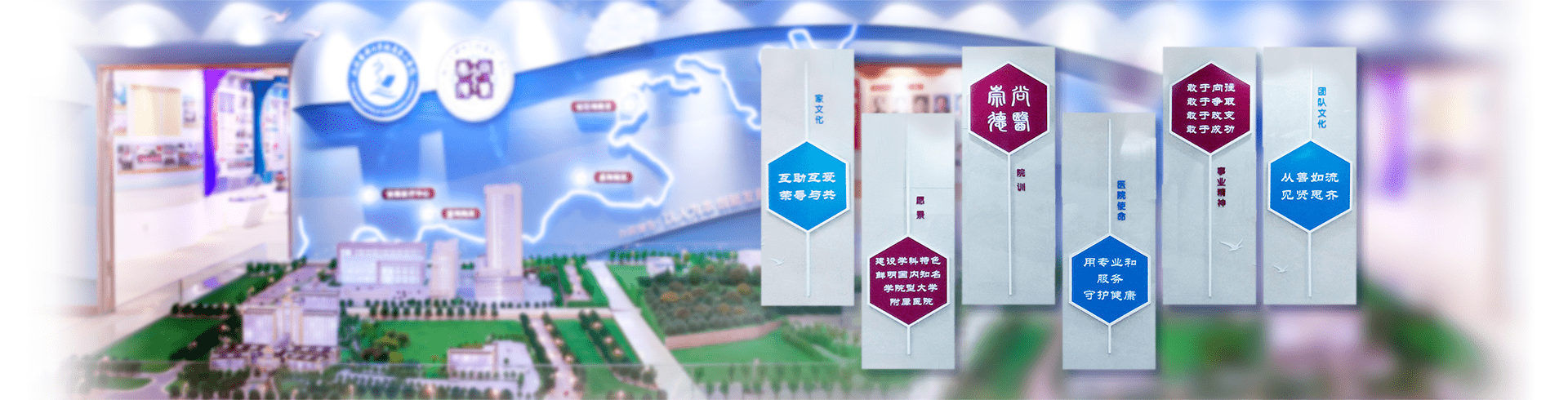如何做可以让病人托付生命的医者?这是我近几年总在思考的问题。
今天我们科学昌明,技术发达,医疗条件好过历史上任何时候。但医患矛盾却在不断加重,患者对我们医务人员的信任在不断下降,医生的尊严和荣誉在动摇。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科学的进步没有必然地带来我们的幸福感呢?是哪儿出了问题?
我想问题是出在人文上,一旦人文缺失,科技就会变成纯粹的工具,人就会异化成服从工具的冰冷机器。人被异化了,科技被异化了,医学人文也被异化了。这是我们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中,我们可以把问题推给社会、推给体制,但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推卸掉的是自己的责任。我们只能更多地从医者的角度来认识,来反思,来自律,来倡导。医学的本真就是为病人救苦解难,我们的工作关乎到病人的生命。只有弘扬大医精神,才能把缺失的人文找回来,把异化的医患关系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所谓“弘扬”就是要把早已存在的、好的东西发扬光大。这个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大医精神,是自古以来中国行医者求仁成圣的追求,是行医者要无限逼近的道德目标。这是中国文化里特有的东西,也是和世界其他文明不同的地方。我们中华文明的终极追求是善,是道德。这既不是希伯来文明的彼岸,也不是印度文明的来世,甚至不是希腊文明的自然法则。我们追求的是与内心一致的善,而且要把这个善外化出建功立业、造福于民的事功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从来没有舍离此世的要求,永生的要求在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行善救人。
因此,在唐代以前,中国的大医们悬壶济世,行走天下,以立功、立言、立德来达到不朽。这种行善的意志就是道德追求,就是“好”的普遍意义。而什么是“好”是可以从自己的内心里得到答案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中国人的做人,就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纯粹的人的追求。“我欲仁,则仁矣”,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需要讲外部条件、社会环境,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样!当然,自己做到了也相信别人会同样做到,这就是“德不孤,必有邻”。这些,都是儒家“心性说”的观念社会化的作用,因为大儒们相信,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人固有之的东西,能天然产生“仁、义、礼、智、信”这些好的标准。
到了孙思邈这儿,大医的追求被进一步提炼成“大医精诚”,不仅秉持了前人的道德追求,而且还给出了道德可欲的标准。他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贱贵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这些是大医行医时的基本要求,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凡求医者均是性命相托,将心比心,所以行医者必应以性命相济,全力以赴。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逻辑是儒家传统文本的根本。
到了宋明理学时期,行善成了普遍常识,“仁义礼智信”是无需再行追问就能确信无疑的基本良知,是一个人何以立世的要求。没了这点要求,则与禽兽无异,为世人不耻。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人会刻意提出要弘扬大医精神,因为不需要,这是常识,就像“人不吃饭会饿”一样妇孺皆知,无需刻意强调。
但五四运动之后,西洋人的坚船利炮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什么是进步和落后,开始了反思和批判。反思和批评都是积极和必须的,但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一样,这场反思和批判运动也有它消极的影响,这个消极的影响就是与我们文化传统的决裂,把两千余年中国人处事立业的人文法则给否定了。对的有可能不对,善的有可能有恶,我们开始了对固有常识产生了怀疑。“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了主流语境,科学精神替代了大医精诚,西方的自然法则统治了中国的人文法则。大医这个具有圣贤光环的名称也逐渐暗淡了,没人再提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了新的道德目标,开始了“六亿神州尽尧舜”的时代。我们每一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都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如何在“狠斗私心一闪念”的运动中纯化自己灵魂的。我们在不断地“斗私”中走进理想,完善个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下过医疗队,都有到田间地头给老乡们看过病,送过药的经历。那时候没人计较个人得失,吃苦受累是为了能改造自己,让自己思想纯化。那时候极少有医患矛盾,医务工作者真的纯洁得像天使。现在的人可能都觉得那时的人太单纯,甚至“傻”!其实这种单纯的背后不正是善的自觉吗?现在的人文缺失不正是社会过于功利,人过于“精”了吗?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终止了这场全民修身运动,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价值判断,也颠覆了我们的常识和理性。在那样一个价值颠倒的年代,“善”成了一个“恶”的符号,道德成了虚伪的代言,我们在非理性中迷失了生命的意义,放弃了终极关怀。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社会进入了一场新的反思和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文化浩劫,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全部,当我们在进行反思和批判这场浩劫时是否要彻底否定我们的文化传统?面对批判所带来的道德缺失我们用什么来填补?尤其是作为我们这些行医者来说,如何才能重回我们的道德高地?我们中国人的信念中没有基督教的彼岸和佛教的来世,没有宗教信仰,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死精神和终极关怀?我们物质发达了,精神却缺失了。这正是我们当下的“痛”!因为我们在物质的繁华中失去了自己,有了白衣天使的危机感。然而,有这种危机感是好事,说明我们医务工作者作为一个整体是不甘堕落的。所以,我们要弘扬大医精神,为我们行医者重建精神家园。有了这种精神,才能使我们行医者安身立命,才能使“救死扶伤”成为不朽。我们只有发大善之愿、怀大爱之心,才能担得起患者的性命相托,才能重新赢得“天使”的荣誉。
“大医精诚”的戒训是我们每个行医者入门的要诀。从跨入医学的门槛那天起,就要日日诵读,一日三省,夕惕若厉,每日必问:病人是我的亲人吗?我是否为他做了所有我应该做的?我是否从治疗中谋了不正当的利益?非此不能行医。医行天下者说到底不光凭借科学,还需要一份爱;不光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所以,决定医生高下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操守。医生= 医学+ 人文。
曾经在与《重生手记》的作者凌志军座谈时,他的话也代表了广大患者的心声:“有些医生是让我真正信服的,是他们同时拥有以下九个特点:一、不自吹自擂。二、不贬低同行。三、不仅关注仪器检查结果,而且关注病人。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肠的人,才能始终保持对病人的耐心和热情。四、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五、对求医者一视同仁。六、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七、不模棱两可。八、言之有据。九、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判断。”
所有的外部规范只是内心要求的帮助,只有内心的善愿才是济世救人的根本,这个根本的标准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你自己的命有多重要,病人的命就有多重要。做到这点,病人便可以以命想托。
(本文刊登于《中国医学人文》杂志第4期,原文摘自凌锋著《梦想成真》 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